一个民族越清楚“我们是谁,我们从何来”,就越能有力把握历史规律,越能使自己行进在历史的正确方向上。从“现代化的迟到国”到“世界现代化的增长极”,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到“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文化自信为实现民族复兴提供了凝聚共识的磅礴力量,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注入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精神滋养。考古新发现中所承载的不仅是中华文明的基因和血脉,也是在探寻“何以中国”中照鉴“未来何处”的一盏盏烛光。
2月19日,备受瞩目的“2024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在京发布,吉林和龙市大洞旧石器时代遗址、陕西宝鸡市周原遗址、安徽淮南市武王墩战国晚期一号墓等六个项目入选。以考古成果来建构百万年的人类起源史和上万年的人类史前文明史,以考古研究来参考、印证、丰富、完善有文字记载以后的文明史,从一年一度的考古新发现中,我们不断领略“何以中国”的文明密码,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文化自豪感。
中华大地锦绣河山,滋养了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并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一代代中国考古学家行走于田野,筚路蓝缕,青灯黄卷,用手铲释读历史,带来了丰硕的考古成果。从1921年的仰韶村遗址首次被发现开始,中国人以考古学的方法正式而郑重地面对自己的远祖,考古人在地层里窥探历史,在陶片中拼对时间,每一个发现都是对自己民族与国家的进一步了解,每一次探寻或多或少都与我们血脉相连,每一段故事都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今天的生活。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目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已实施20余年,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形成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并提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每一项考古新发现,都在不断填补历史链条上的缺环,拓展形成新的历史认知。
比如,此次入选的浙江仙居县下汤新石器时代遗址贯穿新石器时代的始终,是中国万年文化史的重要实证,为研究区域文化演变和万年稻作农业史提供了连续性新材料;甘肃临洮县寺洼遗址马家窑文化聚落展现了5000年前黄土高原西部早期社会的发展水平和文明化程度,填补了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黄河上游核心腹地关键时期的空白,极大丰富了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内容及模式;陕西宝鸡市周原遗址发现王家嘴先周文化大型夯土建筑群,以及西周时期宫城、小城、大城三重城墙,提供了中国城市发展史不可或缺的研究资料……打开封存的“时间胶囊”,提升历史画面的“分辨率”,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更加璀璨夺目。
正是通过对珍贵历史文物的考古发掘与阐释,我们得以更好了解先人的生活方式、思考方式、审美取向等,不断深化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与认识,为推动文化传承发展点亮前进之路。近年来,良渚申遗、殷墟“出圈”、三星堆上新等话题频上热搜,“考古盲盒”等文创产品供不应求,众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遗址博物馆成为网红打卡地……曾经的冷门学科逐渐“热”了起来。无声的历史文化遗存,正以生动鲜活的方式与公众跨时空对话。让历史的轴线再延伸,让历史的信度再增强,让历史的场景活起来,不断推动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持续增强人们的文化认同。我们在感佩诸多考古新发现的同时,文化自豪感与自信心也在凝聚升腾。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历史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和旺盛的创造力,是一个能够不断创造新的历史、新的文明的伟大民族。从“现代化的迟到国”到“世界现代化的增长极”,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到“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文化自信为实现民族复兴提供了凝聚共识的磅礴力量,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注入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精神滋养。考古新发现中所承载的不仅是中华文明的基因和血脉,也是在探寻“何以中国”中照鉴“未来何处”的一盏盏烛光。
一个民族越清楚“我们是谁,我们从何来”,就越能有力把握历史规律,越能使自己行进在历史的正确方向上。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以坚定的文化自信为基础,使文化自信的涵养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相互促进,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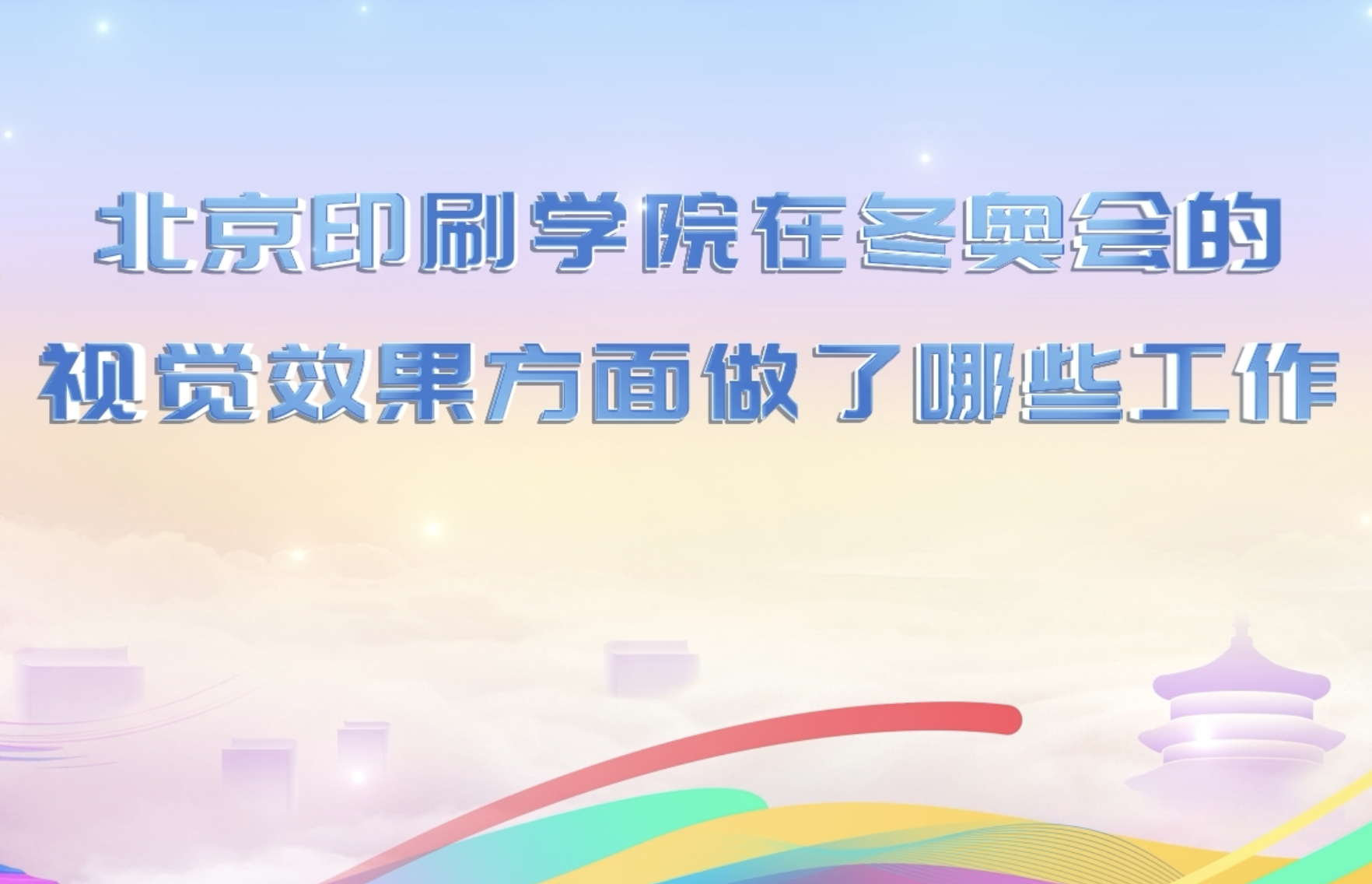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11202003959号
京公网安备11011202003959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