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学新,是一位从事了文博事业30多年的专家。从文博专家到“长城守护人”,他以赤子之心克服重重困难,在长城守护的路上矢志不渝,在考古、遗址调查、文物保护、文化挖掘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洞见长城》第一季(我和长城),带您走近文博专家范学新的“长城梦”。
种下“长城梦”
1992年,范学新怀着对文博浓厚的兴趣,从西二道河中学调到延庆文物管理所工作。面对全新的岗位和行业,他刻苦钻研、潜心学习,把文物知识都制作成了学习卡片,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提高学习效率。同时他还利用自己的特长,开发了一套DOS程序,让文物档案统计与存档更好地适应了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凭借着丰富的知识储备和技术优势,范学新迈进了文物研究和保护的专业领域。
由于长城文物不可收藏,暴露在大自然及风霜雨雪之下,因此比一般文物更脆弱,也因为长城文物不可避免地与参观者密切接触,所以它更容易受到损害。为了更好地保护长城,早在2005年4月4日,延庆发布了《关于启动“长城保护行动”的通知》,并颁布了《延庆县长城保护行动纲要》,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摸清延庆长城的“家底”。从2006年开始,北京市文物局、国家文物局先后启动了长城资源调查工作,也正是从那时起,范学新和他的团队走上了一条长达三十多年的长城实地踏查、研究保护之路。
“这些年北京市文研所(现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古建所,还有市文物局的一些专家老师会经常地到延庆考察研究,这几十年来我也是跟着他们脚步,边工作边学习。”范学新说道。在范学新的记忆里,像汤羽扬老师这样的多位长城专家们,多年来始终坚持脚步为亲,身体力行走遍延庆长城沿线角角落落了,讲长城知识,传播长城文化,让更多的人对长城有了更加立体的认识。“吴梦麟老师和罗哲文老师是我们文博界的老前辈,他们对延庆长城有着很深的感情,对延庆文物也是了解非常透彻,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这对咱们北京地区,包括延庆的文物保护工作,奠定了很坚实的基础。”范学新说道,“这些老先生那种严谨的治学精神,他们对这些文物的那些热情,一直感染着我们,也时刻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步履不停,坚持做下去。”
把党支部“建”到长城上
走得越多,离长城越近,越被长城感染和震撼。长城是坚固的,同时也是脆弱的。古老的文明在召唤,范学新深知,他们有考察长城的责任,也有保护长城的义务,而捍卫长城的心愈加坚定。从2005至2008年,范学新带领长城调查组徒步行程数千公里对延庆境内明长城和部分明以前的长城进行实地调查和测绘,他们辗转山野、跨越荆棘、迎风霜、沐雨雪,实测长城179公里,敌台近500座,城堡40余座,为今天长城保护和管理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长城调查的过程当中,大家走累了、干累了之后,大伙就唱唱歌,鼓鼓劲儿,讲讲笑话,讲讲故事,大家以苦为乐。”范学新说道,“我记得在当年我们文化委员会七一党支部总结大会上,提出一个概念叫作把支部‘建’在长城上。在这种精神影响下,大伙一起完成了大量长城调查工作。”
沿线村落里的“长城密码”
几百年来,长城在延庆文化中印上了深深的烙印。长城踏查不仅摸清了延庆长城的“家底”,更在实地走访调查过程中,对长城沿线各村落间形成的长城文化有了认识和了解。范学新认为,在长城文化带建设的今天,做好长城文化价值发掘和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工作,显得尤为重要。2008年,范学新开始主持《延庆县古村落壁画调查与研究》课题,其中永宁火神庙壁画,反映了明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长年争战与防御这一历史事实,是延庆地区作为南北交融、军事防御要塞的真实写照。壁画中出现的各种元素,诸如敌台、城楼和城墙,连枷棍、火铳这样的兵器,各种信号旗帜,明代军服以及军乐队等内容,对于研究明代军事制度和长城沿线的战争,研究民间花会和民间音乐等地方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长城文化,不仅仅是我们眼见的墙体、壕堑、敌台、城堡、烽燧等有形的实体遗产,它所蕴含的丰富的军事文化、风土人情、民间习俗等无形的文化遗产散落在民间。在八达岭镇石峡村流传着反映闯王进京的河北梆子《三疑记》,在永宁南关村保留着以昭君出塞故事为主题的竹马舞,在永宁太平街还流传着表现军队列阵和击鼓的老秧歌等文艺形式。这些蕴含着长城文化的民间艺术形式,至今仍然焕发着他们的魅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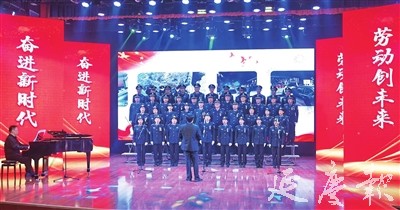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11202003959号
京公网安备11011202003959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