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介绍
丁利娜,现为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长期从事田野考古一线工作,为首都文化事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2014年荣获“北京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21年荣获中宣部“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及“首都最美巾帼奋斗者”称号,2024年入选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及北京市第十五次妇女代表。近年来主持中宣部人才培养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北京社科基金项目等国家级、省部级科研课题7项,出版专著2部,合著3部,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取得了金中都考古发掘与研究的突破性进展,深化了金中都作为北京“都之源”的城市价值,为讲好北京故事、打造北京历史文化金名片提供了重要素材。

北京市宣传思想文化高层次人才培养资助项目
《北京建都之始——金中都城墙遗址考古研究》
金中都是北京建都之始。公元1153年,金帝完颜亮迁都燕京(今北京),改称“中都”,开启了北京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首都的辉煌历程,也为其后元、明、清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于此奠定历史根基。今天的北京,拥有超过870年的建都史、3000余年的建城史以及50多万年的人类生活史,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与博大精深的伟大见证。
金中都遗址位于今北京市西南部,地跨西城区和丰台区,是一座由外城、皇城、宫城三重城垣相套而成的都城,总面积约25平方千米。目前地表尚存的三段残城墙均位于丰台区境内,1984年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是北京古都风貌的重要实物遗存。
城墙与城门作为古代都城的关键组成部分,既是城市防御的核心设施,更是彰显礼制与统治思想的建筑标志。近年来,对金中都外城西、南城墙及端礼门遗址的系统考古发掘,进一步夯实了金中都作为北京“都之源”的实物依据,也让我们对这座都城的城市结构、功能布局与文化内涵,有了更具体而深入的认识。
一、固若金汤的城池——中都城的营建史实
天德二年(1150),金帝完颜亮采纳“惟燕京(今北京)乃天地之中”的建议,下令征调民夫八十万、兵夫四十万,正式启动燕京城的营建工程。天德四年(1152),燕京新宫落成。贞元元年(1153),完颜亮“以迁都诏中外”,改燕京为中都,设大兴府。直至贞元三年(1155),中都城主体营建工程基本告竣,前后历时约五六年。

图一

图二
城垣遗址的考古发现,为我们重现了870多年前中都城的建造实况。因迁都仓促,工期紧张,外城墙的营建因地制宜,随形就势,不一而就。在土质坚实、地基稳固的区域,城墙平地起建,拔地而起;而在土质松软、地基欠佳区域则别具匠心:先开挖深约80厘米的地下基槽,填满碎砖石并夯实,再于基槽中密植长木桩(图一)。这些木桩向下扎入墙基,向上延伸至墙身,既像“地钉”一样加固基础,又作为“永定柱”强化墙体结构,构思巧妙,一举两得。为进一步增强土墙的坚固性,金人以圆头夯具逐层夯筑墙体,形成厚约5~15厘米的夯层和直径约3~13厘米的密集夯窝(图二)。根据考古地层,金中都城墙起建于现地表以下2米处,基础宽24米,墙体残存最高2.5米,复原高度可达16米,规模宏大、气势巍峨。
为提高作战效率,城墙外侧还增筑了用于防御的马面,平面呈圆角梯形,面阔20米,进深约8米,外围包砖加固。马面突出于墙体外侧,可三面迎敌,有效弥补了城墙防守死角,提升了布防灵活性。在距马面约10米处,考古发现了金中都外城的护城河遗迹,河道深约2米,宽度达66米,这一尺度在古代都城防御体系中较为罕见。如此设计很可能与宋代以来火炮使用及填壕战术的发展有关。面对攻城手段的升级,都城防御理念逐步由传统的“城高池深”向“城高池阔”演变,通过拓展防御半径以应对新的军事挑战。
高大的城墙、宽阔的护城河以及密集的马面,共同构成了金中都坚固的城防体系。史载,金末中都曾四次成功抵御蒙古大军围攻,其坚不可摧,可能正得益于这套“城高池阔”的先进防御体系,彰显了金代在军事工程上的创新与智慧。
二、端正礼仪之门——端礼门蕴含的文化内涵
端礼门位于金中都外城南垣西侧。“端礼门”之名,源于儒家“五常”中的“礼”,意为“端正礼仪”。与之相应,东、西、北三面城垣还设有施仁门、彰义门与崇智门。这套命名系统不仅深植儒家伦理,其方位布局更暗合五行学说,将道德理念融入空间秩序,体现了金朝对汉文化的深度吸收与创造性运用。

考古发现的端礼门遗址由两侧墩台与中间门道构成,东西总面阔30米,进深18米(图三)。东、西墩台为门楼基础,基部以三层垫砖铺砌,层间夹以夯土加固,结构坚实。其上为逐层夯实的台基,残高0.8米。门道宽约6米,中部保留将军石基础,路面可见明显踩踏痕迹与数条南北向车辙。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北侧路面残留数个疑似马蹄印迹,还原了当年端礼门内外车马穿行、往来不绝的景象。在城门外侧有瓮城,平面呈马蹄形,东西最宽39米,南北最长28米。瓮城北侧与主墙相连,形成护门小城,其作用在于诱敌深入后形成“瓮中捉鳖”之势,从而有效阻滞敌军。端礼门附近出土的大量摆放整齐、大小不等的石礌等作战工具(图四),生动再现了870多年前战火纷飞、矢石如雨、浴血守城的激烈战况。

考古研究证实,金中都端礼门的规格为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单门道、过梁式门楼,与唐宋以来都城侧门的等级规制高度一致,显示出女真帝王对中原都城制度的继承。作为金中都外城西南门户,端礼门主要供中低级官吏、工匠、杂役及外国使臣等人员通行,同时也是物资运输与军事布防的重要通道。
三、文化融合之城——中都城的多元与统一
金中都的创建者完颜亮,是一位对汉文化极为推崇与仰慕的女真帝王。营建中都之初,他便有意仿效北宋东京汴梁的规划,在辽南京旧城基址上向东、西、南进行扩展,从而形成“外城—皇城—宫城”三重相套的都城格局,以核心宫殿大安殿所在的南北一线为中轴线,两侧建筑对称分布,充分体现了皇权“居中”“居正”“居高”,延续了唐宋以来日趋成熟的都城模式。其方形外城与每面三门之制,契合《周礼·考工记》所载理想都城的模式,以“仁、义、礼、智”命名的四面城门,更是凸显了儒家伦理的文化内涵。
防御体系上,金中都构筑了“城高池阔”的坚固系统,反映出女真统治者从宋金战争中吸取经验,创新性地融合了多民族的军事智慧。城市格局方面,金中都城在原辽南京区域延续了唐代封闭式的里坊结构,而新扩建区域则采用宋代以后兴起的开放式街巷,形成“双制”并存布局,是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上唐宋变革重大转型的实物例证。
此外,金中都的水系与园林营建也别出新意。除沿用辽南京原有湖泊岛屿外,特意将莲花河纳入城内,既保障了宫苑用水,也提升了城市的山水景观品质。在宫城与皇城内设置多个园林区,如宫城中的鱼藻池、皇城周边的东、西、南、北四苑等。同时,在城外近郊营建数量众多的离宫别苑,如西郊钓鱼台、东郊长春宫、城南建春宫、城北万宁宫,以及香山、玉泉山行宫等。金章宗时更在西山敕建“八大水院”,以满足驻跸行苑之需。这些星罗棋布的水苑宫囿,点缀在中都城内外,形成一幅微缩的“捺钵图”,延续了女真民族春水秋山、渔猎巡狩的传统习俗。
总体来看,金中都城布局严整、礼制鲜明。它既继承和吸收了中原都城规划中的礼制思想与农耕文明定居传统,又保留了北方民族捺钵文化的流动特质,在空间结构与制度文化层面均呈现多元融合的倾向。正是这种交融性,使得金中都成为中原文化与女真习俗深度整合的典范,也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过程的有力见证。
北京因“都”而立,因“都”而兴。金中都作为北京建都肇始之城,是其多元与包容文化精神的历史缩影。深入挖掘金中都的文化内涵,对于传承古都文脉、推进首都文化建设,具有深远而重要的意义。
(供稿单位:北京市文物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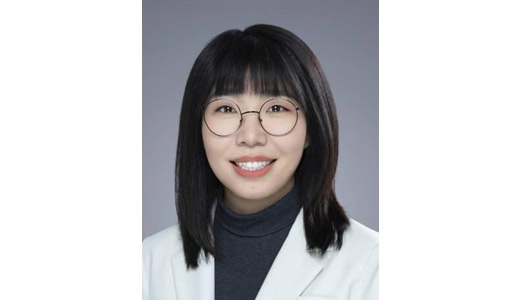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11202003959号
京公网安备11011202003959号
